The Roads to Modernity
作者在本書的前言提到她寫作本書的動機在於她發現英國的啟蒙與法國的啟蒙是如此的不同,甚至遠超過她所預期的。本書的定位並非在於要寫出一本概論性的書,而是一本解釋性的作品。在序言中,作者說明她企圖要重新審視啟蒙,重新回頭討論英國的啟蒙。作者認為,英國發展出了一種和法國啟蒙十分不同的啟蒙。她認為英國的啟蒙除了是個智識運動外,也是個社會運動。本書是以觀念史的方式來探討,處理理性與宗教、自由與美德、自然與社會等等的觀念,這些觀念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塑造出了一個在這三個國家中獨特的啟蒙。她指出,法國的啟蒙哲士們對當時的英國讚譽有加,十分推崇培根、洛克以及牛頓等人的理論與方法,而這些英國的觀念啟發了他們自己的啟蒙。所以她要將英國帶回到歷史舞台的中心,來重新定義啟蒙的觀念。相較於法國以理性價值為主的啟蒙,英國的啟蒙是以美德為中心,而這不是「個人的美德」,而是指「社會的美德」。他們將理性放在次要的地位,扮演著工具性的角色。
本書的第二章便進一步地探討英國的啟蒙。她認為英國沒有像法國那樣的反權威的哲士,有的是一群道德哲學家。這反映出英國啟蒙在社會情感和宗教性上的傾向。英國的這些哲學家並沒有像法國哲士那樣反對宗教,並不強調對宗教權威的批判,至少在情感上是如此,像柏克萊甚至是一個主教。這是作者所探討的第一點。接著,作者從「亞當斯密問題」著手,開始討論英國啟蒙的另一個特色:政治經濟學和道德哲學。「亞當斯密問題」指的是亞當斯密的兩部名著:《道德情操論》及《國富論》乍看之下所顯示出的矛盾。也反映出以追求利益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與以個人正義為核心的道德哲學調和的困難。這個對當代人來說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經過多年的研究已不再認為當中有這麼大的矛盾。作者討論了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觀念,他提出自由放任的貿易制度,反對政府強加其上的特惠或限制。他贊同濟貧法的概念,然而他反對替窮人建立需要的住所。他認為這會限制住他們的流動性以及他們改善生活的機會,也使得他們無法享有其他英國人所享有的自由。亞當斯密和休謨都認為人性中有一個基本的平等,這個概念與早先的洛克等人不同。其實這都反映出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學與道德哲學的一致性。第三點,作者探討柏克的思想。柏克往往被歸類為反啟蒙的,然而作者引用波考克(J.G.A. Pocock )的觀點,認為柏克是一個啟蒙人物,他自認為在護衛啟蒙歐洲免於受到革命份子的影響。柏克從未攻擊啟蒙,他是在自由及多元的基礎上反對法國大革命。他本身是早期啟蒙之子,承繼了洛克和孟德斯鳩,他所反對的是伏爾泰的反基督教以及盧梭所抱持籠統而情緒導向的啟蒙。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英國啟蒙與法國啟蒙的極大不同處,所以他贊同美國革命而反對法國大革命。道德哲學家將道德情操視為社會美德的基本,柏克接受了此一傳統並且更進一步地,將人的情感、行為及道德意見視為社會的基礎。所以在他眼中,法國大革命是個道德上的革命,對他而言這是萬萬不可的。接著,作者又從激進異議份子、衛理公會以及社會上的慈善事業這幾方面探討了當時英國的社會。
第三章則回過頭來談法國啟蒙,作者在這章的開始提到這三種啟蒙的不同有著許多不同的因素:國家的政治性格不同、政治體制中階級關係的不同、教會的本質與權威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經濟上工業化的程度不同、所受到的政府規範也不同,以及其他種種的歷史與社會環境因素。她從幾個層次上來談法國啟蒙:理性與宗教、自由與理性、開明專制與普遍意志、人民與大眾、啟蒙與革命。對啟蒙哲士(philosophes)而言,理性就像是一個咒語一般,是良善信念及正直心靈的記號。他們認為理性對於哲學家,就正如同恩典(Grace)對於信徒一般。這些啟蒙哲士中,有些人是無神論者,有些人例如伏爾泰,則是自然神論者。大體上他們主張宗教寬容 ,具有反閃(anti-Semitism)傾向。理性也將哲士們帶到自由這個概念。然而大多數的啟蒙哲士並沒有有系統地討論政治和社會的組織,杜果(Turgot)和孟德斯鳩是少數的例外。孟德斯鳩的思想體現了在當時自由扮演著一個模稜兩可的角色,他並不將理性視為政治社會的基本原則,而是強調一個政體的精神以及其實際遇到及歷史上曾遇到的情況。他認為宗教在其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非理性。他對當時的教會有所批評,然而他更討厭無神論。另一方面,在其他啟蒙哲士提出的政治理論中,常常是以貴族為核心的。他們認為貴族是捍衛法國政體使其不至於成為君主專制的重要力量。他們並不強調資產家或無產者的觀點。法國啟蒙也引導出了普遍意志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下君主們主張他們代表著這種普遍意志,於是便強調法治,作為其代表普遍意志的證據。基本上她認為法國啟蒙哲士所關懷的對象不是一般人民。英國賦予所有人道德感及常識,法國的理性觀念則有所限制,並沒有擴及一般平民,也沒有像英國那樣的道德性或社會性的成分。同時,法國也不像英國那樣將憐憫置於其道德哲學的中心,也不主張普遍的公民教育。這些都反映出他們對平民的態度。這一章中最後總結處則探討法國啟蒙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認為羅伯斯比等人確實受到盧梭等的影響,而革命者從啟蒙繼承的最明顯的一點是反教權的傾向,而同樣地革命份子也缺乏對底層人民的照顧方案。在這些方面法國革命確實體現了法國啟蒙的特質與侷限。革命者所想要達成的不只是改變法國的社會制度,更是想要使全體人類得到新生,這則體現出法國啟蒙思想中的普遍性。
第四章則是論到美洲的啟蒙,以自由的政治為標題。認為自由是美洲啟蒙的動力,所以是政治理論啟發了美國憲法來支持起這個新的共和國。在美國建國初期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的爭論體現出了美洲啟蒙的性質,聯邦黨人在回應反對的聲音時,強調憲法的基本原則是要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合宜地同時顧及個人及各州的權利與自由。他們試圖在政府的主權及人民的自由中達成一個最好的平衡,最難的是這需要在一個廣大的商業共和國的脈絡下達成。傑佛遜認為革命是不斷進行中的,自由是以流血來不斷更新,受到人權宣言的影響,他認為沒有社會可以建立起永恆的政體或永恆的律法,這個世界永遠是屬於活著的世代的。所以當代的人是他們自己的主人,應該以自己的方式來管理。柏克反對抽象地尋求以理性來建立國家,而沒有正確地評估意見和偏見在人類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潘恩反對柏克的看法,而跟傑佛遜比較接近,認為每一個世代的人對自己有絕對的主權,不被任何事所限制,只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性及權利。作者認為美國開國者精神中的這種自由的政治是美德的必然結果,而社會道德與政治自由的關係正是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爭論的中心。開國者們在為他們的新共和國創立新的政治組織時,並沒有要依賴美德多過理性。然而他們確實在塑造民族的美德以作為穩定的政治基礎上,賦予了美德極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美洲啟蒙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成分,那就是宗教,因為開國者大多是當年尋求宗教自由者的後裔,美洲大陸是個深具宗教性的地方。在憲法中並沒有出現美德或宗教的字眼,然而實際上這兩者都已被預設為根值於人性之中的,這反映在人民的美德以及社會的傳統之中。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宗教便沒有美德,沒有美德便沒有自由,沒有自由便沒有辦法建立共和政府。這一章的最後,作者引用了一段美國憲法的前言:「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建立一個更完美的聯盟……」美國憲法並沒有說是完美的,而是說更完美的,英國的道德哲學家們會為這種謹慎的情操背書,法國的哲士們可就不會這樣做了。
在結尾的一章,作者認為在今日的美國,啟蒙仍持續著。就正如同美國的建立是如此的獨特,美國啟蒙所建立在其上的基礎也是如此。而美國也獨特地持續投身於啟蒙之中,當年啟發開國者的那些心智的習性、心靈的性情都仍舊啟發著現在的美國人,在法國或英國並沒有這種情況。當年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第一共和早已被推翻取代,今日用來裝飾法國外相辦公室的不是伏爾泰或盧梭的畫像,而是拿破崙。所象徵的是軍事的榮耀與興衰,這一點都不是法國啟蒙的精神。在 英國也好不到哪裡去,亞當斯密的權威在他死後十年便被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反駁。十九世紀末葉,馬歇爾(Alfred Marshall)試圖恢復經濟學中的道德面向,馬歇爾說這是亞當斯密式的。然而這很快便被國會中的自由黨人所推翻了。英國的道德哲學家們在今日並有像稍早之前的哲學家霍布斯和洛克這樣負有盛名,同時他們所重視的社會道德:同情、憐憫與慈善也缺乏像古典道德:英雄、勇氣、智慧這樣的崇高性,然而仍值得嚴肅地看待與尊崇。作者認為,英國啟蒙的哲學在美國引起的迴響比英國本土還大,美國吸收了英國啟蒙的思想並使之保存下來。美國發揚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並且復興了美德在政治及社會中的價值。隨著美德在公共意義上的恢復而來的,是美德的價值在個人意義上的恢復,也就是憐憫的社會美德。這是英國啟蒙的獨特貢獻,將原本宗教性的美德轉換成世俗性的,使個人的責任成為公共的職責。作者提到,蓋伊(Peter Gay)認為在法國對於廢除刑求的抗爭,是人類理性意志的展現。她認為相對地,在英國要求廢除奴隸的運動則不是由理性所引發的,而是人道主義的熱情的展現,是由於憐憫而非理性。最後,作者認為美德的社會學、理性的意識型態、自由的政治到現在仍引發共鳴,然而不論是美德、理性還是自由,這些都不是那個時代才出現的,也不會被後現代所取代或逼退。今日的我們,對於這些英國道德哲學家、法國啟蒙哲士以及美國開國者所處理的人性、社會以及政治,仍在真實與謬論、假設與堅信之間掙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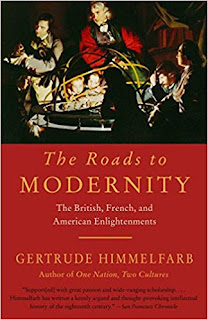


留言